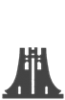9月21日,第十七届新莫干山会议召开,来自全国各地著名经济学家、智库专家与中青年学者和企业代表等60余人,围绕“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和政策选择”“中国本土现代经济学的创新探索”两个主要议题进行研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中欧陆家嘴金融50人论坛首席专家、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参加会议,并向大家分享了在中国人民银行调统司工作期间,组织中国独创的重要宏观经济学指标“社会融资规模指标”的经历,以及该指标从研发到广泛运用乃至今天国际承认的始末。
盛松成教授认为,社融与实体经济相关性较强,直接受宏观政策的调控,甚至对经济具有一定领先性。此外,社融中企业债券融资、表内外融资等对利率都很敏感,其敏感性已经超过M2,所以社融成为我国金融宏观调控的重要监测指标和中介目标。8月社融存量增速比上月提高0.1个百分点,在主要金融指标中率先触底回升,反映出8月很可能是我国经济迎来企稳回升的转折点。目前我们仍然要坚持宏观经济逆周期调控,力度不宜减弱。
以下为盛松成教授发言主要内容:
如今社融的定义已为人熟知。社会融资规模是指一定时期内(每月、每季或每年)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额。社融是通过金融机构的资产方和金融市场的发行方统计的,具体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实体经济从金融机构的表内融资(人民币贷款、外币贷款);二是表外融资(委托、信托贷款和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三是直接融资(债券和股票融资);四是其他方式向实体经济提供的资金支持。此处其他方式包括保险公司赔偿、投资性房地产、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和贷款公司贷款等。
2018年7月起,社融指标进行了一些修订,人民银行陆续将“存款类金融机构资产支持证券”“贷款核销”“政府债券”等纳入社融统计指标。统计指标修订很正常,例如历史上美国M2指标就曾多次修订。社融指标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也支持对其予以修订。例如,贷款核销是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应该加进去;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券也主要由金融机构购买,并通过金融市场发行。尽管经过数次修订,但万变不离其宗,社融反映的是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这个概念始终没有变。
要做出一个中国独创的新指标不容易。2010年9月,我担任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按照行领导要求,11月初调统司开始研究编制社融指标。国务院和人民银行领导对社融编制高度重视,多次批示要求听取各方面意见,期间与银、证、保、发改委等多个部门反复协调。可以说,该指标是集体智慧结晶,我只是起了牵头人和主要责任人的作用。因为是我国首创,很多内容都经过反复斟酌修改,如该指标定义短短的一句话就是我在出差的飞机上修改确定下来的。“社会融资规模”的名称也是我建议的。当时考虑过“社会融资总规模”或者“社会融资总量”,但我建议还是“社会融资规模”比较好,因为称为总规模或者总量可能不准确,毕竟有些内容没有包括进去,就不能称之为总量。事实证明的确如此,社融指标后续作了新的补充。
2011年4月我们首次发布社融指标,当时人民银行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引起社会广泛关注。2012年起我们做到了按月发布,并在2012年9月公布了2002年以来的月度历史数据。2014年起按季发布地区社融增量数据。因为货币供应量M1、M2有同比增速数据,于是各方面都希望社融也能做出同比增速。增量的同比增速短期内上下波动很大,缺乏指导意义,因此我们需要基于社融存量数据计算同比增速。然而,做存量数据很困难,很多数据不在我们这里。通过协调各有关方面,用了整整两年,于2015年按季发布社融存量数据,2016年1月起,按月发布社融存量数据,于是有了目前按存量计算的社融同比增速。
经过20年发展,社融增量从2002年2万亿元增长到2022年的32万亿元。这里可能大家会有疑问,社融指标是2011年才诞生,为何会有2002年的数据。其实这是我们倒推所得。很多统计的历史数据都是倒推得到的。例如,直到上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才开始编制广义货币供应量M2指标,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安娜·雅各布森·施瓦茨所著《美国货币史:1867-1960》一书将该指标倒推回溯了近100年。
社融是我国独创的金融指标。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社融指标?由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体制更为完善,利率传导机制顺畅,长期以来更注重使用价格型指标而非数量型指标。同时,发达国家金融机构资产端高度复杂、数据统计成本很高。
尽管西方国家尚未有类似实践 ,却很早就有相关的理论研究,为社融指标的诞生提供了理论基础。我们知道,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链条”中,从金融机构资产和负债两个角度出发,可分为货币渠道和信用渠道。20世纪50年代,托宾、施蒂格利茨及伯南克等经济学家就陆续提出了货币政策传导的“信用渠道”,强调货币政策的变化通过改变商业银行的贷款量(资产端)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方和金融市场发行方(如信托贷款、债券融资、股票融资等的变动)来影响企业资金可得性,改变私人部门投资和最终产出。结合我国实际,笔者曾在《中国货币政策的二元传导机制——两中介目标,两调控对象》(发表于《经济研究》,2008年第10期。该文的英文翻译版《The binary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China’s monetary policy-A reaserch on the “two intermediaries, two targets” model》刊登于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 2009,4(3):335-360.)一文中,揭示了信贷指标(也就是金融机构的资产端)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在现实中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属性。社会融资规模则是上述理论和实践在我国宏观金融调控中的进一步延申。
我国尤其重视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这是我们编制社融的初衷。首先,尽管我们有货币供应量M0、M1、M2,但这些指标难以清晰反映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第二,社融具有丰富的结构内涵,多角度、全方位反映各类融资支持实体经济的状况,符合金融宏观调控的需要。第三,长期以来,西方主要国家更注重价格型指标而非数量型指标,由此导致的信息缺失进而监管不力,正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首创的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开国际先河,反映了我国为弥补统计信息缺口而做的努力,具有很高的开放性、可塑性,日渐被社会各界接受与应用,也得到了IMF、BIS等国际金融组织的认可。
社融广受社会关注。首先,中央重视。自201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以来,社融每年都会写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保持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其次,地方看重。2011年社融指标问世后,从省级到县级都想做地方的社融指标,但是各地自己做不仅耗时耗力,而且会产生指标体系差异问题,因此我们决定统一编制分地区的社融数据。人们无法知道M2有多少留在北京,多少留在上海,而社融都能反映。社融能够反映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期限、不同融资方式的资金,比如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等表外融资、股票和债券等直接融资、国债和地方债发行等。社融产生前,地方政府主要看重人民币贷款,现在通过社融还能够知道直接融资、表外融资等对当地经济的支持。第三,市场关注。最近10多年来社融和M2已经成为我国最重要的两大金融宏观监测和调控指标。第四,学界研究。现在讨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现高质量发展等学术论文中经常会采用社融指标。2016年我与合作者所著《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政策传导》一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并获得2020年浦山政策研究奖。我们欣喜地看到国内外关于社融的学术论文越来越多,说明我国独创的金融指标正走向学术舞台。
社融不仅仅是一个统计指标,而且在宏观调控中发挥着积极作用。首先,社融与实体经济相关性较强,直接受宏观政策的调控(如降准降息、政府债券发行等),甚至对经济具有一定领先性。其次,社融中企业债券融资、表内外融资等对利率都很敏感,其敏感性已经超过M2,所以社融成为我国金融宏观调控的重要监测指标和中介目标。第三,社融指标全面和前瞻性反映我国经济金融运行,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向高质量发展。
最新社融数据显示,8月很可能是我国经济迎来企稳回升的转折点。8月社融增量为3.12万亿元,同比多增6316亿元,8月末社融存量已经高达368.61万亿元,同比增长9%,增速比上月提高0.1个百分点,在主要金融指标中率先触底回升。8月,我国居民部门短期贷款同比多增398亿元,说明消费正在逐渐恢复;虽然居民中长期贷款同比少增1056亿元,主要受到前期房地产市场销售偏弱以及居民提前还房贷的影响,但后续房地产政策的不断推进可能带动居民中长期贷款增长。8月地方政府专项债加速发行,政府债券净融资1.18万亿元,成为社融最主要推动力;9月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规模仍较大,将拉动基建投资,有助于在较短时间内推动经济企稳。如果9月数据继续向好,那么四季度很可能会像一季度那样,经济会有较好的表现。目前我们仍然要坚持宏观经济逆周期调控,力度不宜减弱。